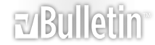“你知道残奥会是什么时候举行吗?”刘德华这个问题总能难倒人。
http://zixun.goufang.com/Images/2008...5145251860.jpg
苏桦伟是三届残疾人奥运会金牌得主,目前伤残人士100米和200米短跑世界纪录保持者,被香港媒体称为“痉挛飞人”;他的正式职业是刘德华歌迷会员工,负责把照片上传到电脑里。
从1996年起,刘德华每年会拿出10万元左右港币资助香港的残疾运动员。每次残奥队返回香港,他还会送每人一块自己订做的“奥运金牌”,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第一名,“金牌是真金的,当然金比较薄”。
今年8月,刘德华作为2008年北京残奥会爱心大使,发布了自己填词的2008残奥会单曲,《Everyone is NO.1》(《每个人都是第一名》),他笑着说,“大家都在抢奥运,没有人跟我抢残奥”。
假第一
1992年7月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,刘德华也是“抢奥运”的一员,他帮香港无线电视台去巴塞罗那录制一个奥运会马拉松特别节目。
刘德华在西班牙无意中得知,原来奥运会结束后1个月左右,还有一个残奥会:“都是拿金牌,都是为国争光,大家关心奥运会,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关心残奥会?”
出于好奇,刘德华决定“关心”一下残奥会。期间他回香港拍了一部电影,腾出时间专门去看残奥比赛。
关心遭到了当时香港残奥会负责人的质疑:刘德华是不是要借残奥会塑造自己的形象?为了撇清关系,刘德华自掏腰包买票去西班牙当拉拉队员。
他看的是男子4×100米接力赛,那是香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:“当时香港挂的还是英国国旗,队员们就把后面的头发刮出了‘HK’的字样。”
结果交接棒失误,香港队输了比赛。回到香港,刘德华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块“奥运金牌”:“什么叫超人,只要对自己负责任,你就是第一名。”
刘德华一直觉得,鼓励一个不及格的人比鼓励一个高分的人更重要:“你给他的鼓励,也许能让他从0分到100分。”
刘德华从小就是第一名,小学升中学考了学校的状元。中一毕业考试,状元刘德华的成绩是全班12名——英文不及格。更惨的是,学校规定英文不及格不能升二年级,状元变成了留级生。
“我一辈子没想过会留级。”回到家,爸爸看到成绩单,二话不说把他狠狠打了一顿,打完了让他跪在历代祖先牌位前面,跪了整整一个晚上,“我真觉得跟世界末日一样”。
当时学校一个姓余的老师,默默帮他找了英文老师,还帮忙付了补习费。第二年再考英文的时候,刘德华考八十多分。“如果没有那个中学老师,可能就没我了。”
2000年,刘德华收到了一个“假奖杯”。那时他凭《暗战》角逐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,颁奖前,香港的电影记者合送了一个塑料奖杯,上面写着:最佳男主角——他之前已经8次角逐影帝未遂了。“大家怕我万一又拿不到,就先送给了我。”最终他获得当届金像奖“影帝”的奖杯。刘德华说,他现在还珍藏着真假两个奖杯。
“‘第一’是个很假的概念,演员怎么跟运动员比?谁又可以说哪个演员是第一名?所以我会在歌里写:‘我的泪不是你的泪;我的痛不是你的痛’。我希望在这次残奥会上,有人能看到伤残运动员,‘每个人都是第一’。”刘德华说。
真第一
“他脾气怪怪的。”刘德华是在1996年一次伤残运动员筹款会上知道苏桦伟的,此时刘德华已经跟残疾人运动员很熟了。大家为筹款拍宣传照,瘦瘦高高的苏桦伟老是挪来挪去,嘴里嘟哝着“运动员不该来干这些”。
苏桦伟天生痉挛、弱听,他听不懂普通话,讲话也有些含混。为了配合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,他从家里捧来了四块真的金牌,分别装在四个盒子里,盒子有些旧,但没有任何灰尘和污点,盒子的角落上工整地写着时间、地点。一个同事开玩笑说要把这些金牌拿去当铺卖掉,他紧张地抱着盒子不肯放手。
他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香港人家里,爸爸是油漆工,妈妈从苏桦伟出生时就辞职在家照顾他,弟弟比他小8岁。一家四口挤在香港九龙爱民村一个小房子里,整个房间加上厨房厕所阳台,不过35平方米。由于痉挛,苏桦伟睡觉时,腿会不自觉地飞起来打在家人身上。
苏桦伟的童年是在家里度过的,他怕吵,家里的电视基本上不开。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就很能跑步,但在妈妈眼里,他并不是天才,反而是“路都走不稳,经常摔倒”。
苏桦伟读的是特殊学校,1994年参加学校运动会,跑完100米后,一个教练走过来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训练——教练叫潘健侣,白天在中学教历史,晚上到沙田香港体育学院训练残疾人田径队。1992年这个义务教练带队首次代表香港参加巴塞罗那残奥会。
两年中,苏桦伟每周训练3天,物理治疗3天。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残奥会,原本并没有苏桦伟,快比赛时,4×100米的一个选手突然出事没法参加,潘健侣抓住苏桦伟顶了上去。那是苏桦伟第二次坐飞机,第一次是1996年初去英国参加英联邦运动会。
“玩一下而已嘛。”当时苏桦伟15岁,不知道奥运和金牌是什么东西,只知道要跑第一。结果 香港第一次获得了残奥会4×100金牌。
苏桦伟从此开始4年一个刻度的生活。
刘德华和苏桦伟熟悉起来是在摄像机里。2000年悉尼残奥会,刘德华作为香港残奥代表,带领选手参加——再没有人怀疑他是利用残奥塑造形象了。苏桦伟的比赛项目是100米、200米和400米。他第一次参加400米比赛,目标是破世界纪录。
刘德华坐在看台上,手持摄像机,帮苏桦伟拍了400米的全过程:“他开始是决赛里面最慢的一个,到后面200米,他真的是一个一个超过别人,然后拿到冠军。”刘德华一直保留着这段录像。
“我以前的经纪人说过,刘德华天分不是很高,每件不在我掌握里的事情,我都会紧张,比如跳舞,必须花很长时间去练、去排才会有把握,否则都会紧张。”刘德华说。
在悉尼残奥会比赛的几天,刘德华和苏桦伟他们一直待在一起,大家已经可以开玩笑了。
“刘德华一直跟我说,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他。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困难。”苏韩小贞说,刘德华当时就让儿子毕业之后去他那里上班,她觉得对方只是客气。
从悉尼回到香港之后,客气的刘德华送了一台电脑给苏桦伟,还帮他付了网费,直到现在。
“第一”无用
“我觉得这是一种歧视。” 苏桦伟刚刚签的经纪人陈恩能说,奥运会前面只要加上“伤残”二字,价值不只是折了一半。
同样是奥运冠军,李丽珊拿一个金牌,《东方日报》奖励100万,康体发展局50万,恒生银行50万,霍英东30万外加一公斤黄金;苏桦伟2000年拿了三金两铜,打破了两项世界纪录,各项奖金加起来不超过20万元。
“我看过香港电台一个介绍他们平常生活的特别节目,有些残疾人运动员根本找不到工作,找到工作的,老板也不会让他去训练。”刘德华说。
奥运会是四年一次,但现实生活不是四年一次。香港没有残疾运动员这个职业,运动员没有固定的工资可以领取。
香港伤残人士体育协会是对口这些残疾人运动员的机构,他们根据运动员的成绩,每年发给运动员一些补贴,拿到奥运金牌的补贴会稍微高一些,没拿到的,补贴就会锐减。苏桦伟的伤残奥运奖学金算是补贴里待遇比较高的,每年有5万元——香港一个清洁工的月收入都不止7000元。
“我有学生半价优惠。”苏桦伟并不认为是歧视。
2002年,苏桦伟的爸爸工作时不慎摔断了腿,由于是私人工作,医疗费也得自己负担,家里惟一的经济支柱顷刻倒掉。此时上一届的奥运热潮已经过去,苏桦伟被夹在了中间:要想参加下一届奥运,平常的训练必须坚持,坚持了训练就没办法上班。
2004年雅典奥运会,苏桦伟荡到了人生最低点:雅典奥运会更改了规定,必须使用起跑机,因此他输了100米和400米,只赢了200米;这一年他正好毕业,每年5万元的奖学金也随之消失。
苏桦伟不得不面对生存的压力,由于他的名气,几家慈善机构倒是愿意请他当文员,但必须按时上下班。苏家一度决定,不跑了。
刘德华算到苏桦伟该毕业了,又问他愿不愿意来自己公司上班,苏桦伟兴高采烈地同意了。
苏桦伟成了刘德华公司里最“大牌”的员工:有时歌迷会活动太过疯狂,苏桦伟的耳朵受不了,其他同事会放下工作先把他带到安静的地方;刘德华上班碰到苏桦伟,会教他变一些魔术,从一堆扑克里选出4张A来;最关键的是,他可以随时停工去训练,工资一分不少。
苏桦伟已经在刘德华的公司工作3年了,他跟老板有个约定,要比一次100米跑。
“你知道殘奧會是什麽時候舉行嗎?”劉德華這個問題總能難倒人。
蘇桦偉是三屆殘疾人奧運會金牌得主,目前傷殘人士100米和200米短跑世界紀錄保持者,被香港媒體稱為“痙攣飛人”;他的正式職業是劉德華歌迷會員工,負責把照片上傳到電腦裏。
從1996年起,劉德華每年會拿出10萬元左右港幣資助香港的殘疾運動員。每次殘奧隊返回香港,他還會送每人一塊自己訂做的“奧運金牌”,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第一名,“金牌是真金的,當然金比較薄”。
今年8月,劉德華作為2008年北京殘奧會愛心大使,發布了自己填詞的2008殘奧會單曲,《Everyone is NO.1》(《每個人都是第一名》),他笑著說,“大家都在搶奧運,沒有人跟我搶殘奧”。
假第一
1992年7月西班牙巴塞羅那奧運會,劉德華也是“搶奧運”的一員,他幫香港無線電視台去巴塞羅那錄制一個奧運會馬拉松特別節目。
劉德華在西班牙無意中得知,原來奧運會結束後1個月左右,還有一個殘奧會:“都是拿金牌,都是為國爭光,大家關心奧運會,為什麽沒有多少人關心殘奧會?”
出于好奇,劉德華決定“關心”一下殘奧會。期間他回香港拍了一部電影,騰出時間專門去看殘奧比賽。
關心遭到了當時香港殘奧會負責人的質疑:劉德華是不是要借殘奧會塑造自己的形象?為了撇清關系,劉德華自掏腰包買票去西班牙當拉拉隊員。
他看的是男子4×100米接力賽,那是香港第一次參加這個比賽:“當時香港挂的還是英國國旗,隊員們就把後面的頭發刮出了‘HK’的字樣。”
結果交接棒失誤,香港隊輸了比賽。回到香港,劉德華給他們每個人發了一塊“奧運金牌”:“什麽叫超人,只要對自己負責任,你就是第一名。”
劉德華一直覺得,鼓勵一個不及格的人比鼓勵一個高分的人更重要:“你給他的鼓勵,也許能讓他從0分到100分。”
劉德華從小就是第一名,小學升中學考了學校的狀元。中一畢業考試,狀元劉德華的成績是全班12名——英文不及格。更慘的是,學校規定英文不及格不能升二年級,狀元變成了留級生。
“我一輩子沒想過會留級。”回到家,爸爸看到成績單,二話不說把他狠狠打了一頓,打完了讓他跪在曆代祖先牌位前面,跪了整整一個晚上,“我真覺得跟世界末日一樣”。
當時學校一個姓余的老師,默默幫他找了英文老師,還幫忙付了補習費。第二年再考英文的時候,劉德華考八十多分。“如果沒有那個中學老師,可能就沒我了。”
2000年,劉德華收到了一個“假獎杯”。那時他憑《暗戰》角逐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,頒獎前,香港的電影記者合送了一個塑料獎杯,上面寫著:最佳男主角——他之前已經8次角逐影帝未遂了。“大家怕我萬一又拿不到,就先送給了我。”最終他獲得當屆金像獎“影帝”的獎杯。劉德華說,他現在還珍藏著真假兩個獎杯。
“‘第一’是個很假的概念,演員怎麽跟運動員比?誰又可以說哪個演員是第一名?所以我會在歌裏寫:‘我的淚不是你的淚;我的痛不是你的痛’。我希望在這次殘奧會上,有人能看到傷殘運動員,‘每個人都是第一’。”劉德華說。
真第一
“他脾氣怪怪的。”劉德華是在1996年一次傷殘運動員籌款會上知道蘇桦偉的,此時劉德華已經跟殘疾人運動員很熟了。大家為籌款拍宣傳照,瘦瘦高高的蘇桦偉老是挪來挪去,嘴裏嘟哝著“運動員不該來幹這些”。
蘇桦偉天生痙攣、弱聽,他聽不懂普通話,講話也有些含混。為了配合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,他從家裏捧來了四塊真的金牌,分別裝在四個盒子裏,盒子有些舊,但沒有任何灰塵和汙點,盒子的角落上工整地寫著時間、地點。一個同事開玩笑說要把這些金牌拿去當鋪賣掉,他緊張地抱著盒子不肯放手。
他出生在一個並不富裕的香港人家裏,爸爸是油漆工,媽媽從蘇桦偉出生時就辭職在家照顧他,弟弟比他小8歲。一家四口擠在香港九龍愛民村一個小房子裏,整個房間加上廚房廁所陽台,不過35平方米。由于痙攣,蘇桦偉睡覺時,腿會不自覺地飛起來打在家人身上。
蘇桦偉的童年是在家裏度過的,他怕吵,家裏的電視基本上不開。他記得自己小時候就很能跑步,但在媽媽眼裏,他並不是天才,反而是“路都走不穩,經常摔倒”。
蘇桦偉讀的是特殊學校,1994年參加學校運動會,跑完100米後,一個教練走過來問他願不願意參加訓練——教練叫潘健侶,白天在中學教曆史,晚上到沙田香港體育學院訓練殘疾人田徑隊。1992年這個義務教練帶隊首次代表香港參加巴塞羅那殘奧會。
兩年中,蘇桦偉每周訓練3天,物理治療3天。1996年美國亞特蘭大殘奧會,原本並沒有蘇桦偉,快比賽時,4×100米的一個選手突然出事沒法參加,潘健侶抓住蘇桦偉頂了上去。那是蘇桦偉第二次坐飛機,第一次是1996年初去英國參加英聯邦運動會。
“玩一下而已嘛。”當時蘇桦偉15歲,不知道奧運和金牌是什麽東西,只知道要跑第一。結果 香港第一次獲得了殘奧會4×100金牌。
蘇桦偉從此開始4年一個刻度的生活。
劉德華和蘇桦偉熟悉起來是在攝像機裏。2000年悉尼殘奧會,劉德華作為香港殘奧代表,帶領選手參加——再沒有人懷疑他是利用殘奧塑造形象了。蘇桦偉的比賽項目是100米、200米和400米。他第一次參加400米比賽,目標是破世界紀錄。
劉德華坐在看台上,手持攝像機,幫蘇桦偉拍了400米的全過程:“他開始是決賽裏面最慢的一個,到後面200米,他真的是一個一個超過別人,然後拿到冠軍。”劉德華一直保留著這段錄像。
“我以前的經紀人說過,劉德華天分不是很高,每件不在我掌握裏的事情,我都會緊張,比如跳舞,必須花很長時間去練、去排才會有把握,否則都會緊張。”劉德華說。
在悉尼殘奧會比賽的幾天,劉德華和蘇桦偉他們一直待在一起,大家已經可以開玩笑了。
“劉德華一直跟我說,有什麽困難就去找他。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麽困難。”蘇韓小貞說,劉德華當時就讓兒子畢業之後去他那裏上班,她覺得對方只是客氣。
從悉尼回到香港之後,客氣的劉德華送了一台電腦給蘇桦偉,還幫他付了網費,直到現在。
“第一”無用
“我覺得這是一種歧視。” 蘇桦偉剛剛簽的經紀人陳恩能說,奧運會前面只要加上“傷殘”二字,價值不只是折了一半。
同樣是奧運冠軍,李麗珊拿一個金牌,《東方日報》獎勵100萬,康體發展局50萬,恒生銀行50萬,霍英東30萬外加一公斤黃金;蘇桦偉2000年拿了三金兩銅,打破了兩項世界紀錄,各項獎金加起來不超過20萬元。
“我看過香港電台一個介紹他們平常生活的特別節目,有些殘疾人運動員根本找不到工作,找到工作的,老板也不會讓他去訓練。”劉德華說。
奧運會是四年一次,但現實生活不是四年一次。香港沒有殘疾運動員這個職業,運動員沒有固定的工資可以領取。
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是對口這些殘疾人運動員的機構,他們根據運動員的成績,每年發給運動員一些補貼,拿到奧運金牌的補貼會稍微高一些,沒拿到的,補貼就會銳減。蘇桦偉的傷殘奧運獎學金算是補貼裏待遇比較高的,每年有5萬元——香港一個清潔工的月收入都不止7000元。
“我有學生半價優惠。”蘇桦偉並不認為是歧視。
2002年,蘇桦偉的爸爸工作時不慎摔斷了腿,由于是私人工作,醫療費也得自己負擔,家裏惟一的經濟支柱頃刻倒掉。此時上一屆的奧運熱潮已經過去,蘇桦偉被夾在了中間:要想參加下一屆奧運,平常的訓練必須堅持,堅持了訓練就沒辦法上班。
2004年雅典奧運會,蘇桦偉蕩到了人生最低點:雅典奧運會更改了規定,必須使用起跑機,因此他輸了100米和400米,只贏了200米;這一年他正好畢業,每年5萬元的獎學金也隨之消失。
蘇桦偉不得不面對生存的壓力,由于他的名氣,幾家慈善機構倒是願意請他當文員,但必須按時上下班。蘇家一度決定,不跑了。
劉德華算到蘇桦偉該畢業了,又問他願不願意來自己公司上班,蘇桦偉興高采烈地同意了。
蘇桦偉成了劉德華公司裏最“大牌”的員工:有時歌迷會活動太過瘋狂,蘇桦偉的耳朵受不了,其他同事會放下工作先把他帶到安靜的地方;劉德華上班碰到蘇桦偉,會教他變一些魔術,從一堆撲克裏選出4張A來;最關鍵的是,他可以隨時停工去訓練,工資一分不少。
蘇桦偉已經在劉德華的公司工作3年了,他跟老板有個約定,要比一次100米跑。